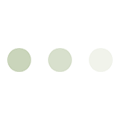《女人·容器》
梁婉莹 雕塑 / 瓷创作这个系列作品的时候,我处在一种非常平和安定的生活状态中。我生活在离我的家乡和亲人约 11600 公里的美国东北部的乡村地区。这里的生活时常勾起我童年在中国农村生活的记忆。尤其夏初的时候,我经常走在院子里欣赏不断冒出来的野花野草,像童年时一样惊奇于它们的构造和多样,在发现和好奇中享受着一种单纯的快乐。 我喜欢花草,可能是受我妈妈的影响。我妈妈非常喜欢花,我们一起散步时如果发现一棵开花正好的树,她会非常高兴,还一定会去合影。我妈妈的快乐一定会影响我,因为她是家里的“大人物”。妈妈掌握着家里的一日三餐,如果一家人一天的三餐能让人满意,那么这一天也不会过得太差。而在我组建家庭之前,妈妈在一日三餐所达到的成就对我来说是透明的。因为我从小就习惯了妈妈每天都在做饭这件事,好像是生活中最正常不过的事情而已。就像那些摆在家里的容器们,是最容易让我们视而不见的东西。 到美国以后,我极其想念妈妈做的食物,以前非常普通的事情变成我现在的大事。这个系列里,我做了几个有镂孔的器物,我想我可以用它们来盛饺子,也可以提醒我:在家庭中,妈妈日复一日那些透明的付出,在多年以后,会在孩子的记忆里慢慢地一朵一朵开成鲜花。让他们突然领悟到,自己平凡无奇的过去也是踩着一朵一朵饱含着母亲祝福的花而来。生活也不过是要继续去把泥土变成花伴随着自己走过。所以在这一系列作品里,我刻意把这些容器做成一种复杂的、好像是很重要的、很有仪式感的形式,大概就是想提醒自己去珍视那些被忽略的日常。

《循环沉积》
孙月 装置 / 玻璃、瓷泥、金属氧化物 4×10×0.2cm×60西方的时间观念是数字的、顺序的、不可逆的。而中国自古对于时间的观念是截然不同的:是文字的、刹那的、循环的。艺术家孙月的作品《循环沉积》由一甲子60个“时间切片”组成。她每日近十六个小时枯坐在工作台前,模仿自然界地质沉积和挤压的过程,用瓷泥浆和金属氧化物交替叠加“沉积”,制造出属于自己时间的沉积层,并在此过程中截取60个时间片段,制作成地质薄片样本。 从第一个切片的单层沉积,经过上千层沉积和挤压,到第六十号“循环”至近似沉积的初始状态,从而与第一片首尾接续。作品试图用泥土探讨认知的边界,用表层的科学、客观、理性,表达东方独有的循环的、混沌的时间观念的作品内核。这60片伪造沉积岩切片,以循环往复的甲子纪年编号,被放置在象征时间形状的鹦鹉螺弧形展区之中,由此进入时间的循环。 “不同于连贯的、线性的、客观的时间,我自己对时间的感受总是片段的、断续的、刹那的、循环往复的。故想做一系列沉积岩切片,利用地质岩石磨片的形式,用看似科学的方法,在视觉上制作出循环的、非现实的时间。我尽力模仿自然界中泥土沉积的过程,试图用泥土的方式记录自己生命的时间。”(孙月)

《等花开》
苏献忠 雕塑 装置 / 德化白瓷 *鸣谢Ting-Ying Gallery艺术家苏献忠的作品《等花开》,花团锦簇、花树错落,繁密花束由一朵朵小花组成,将传统捏塑工艺发挥到极致,并在当代语境下有了新诠释。做“花”是苏献忠的家族传统,他的曾祖父、德化著名制瓷大师苏学金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凭借作品《梅花》获得金奖,每代传承人都在做“花”上持续开拓,花也不停地绽放。《等花开》是苏献忠久违的花主题创作,在2020年疫情期间来了灵感,从3月初一直做到10月底,纯粹的自然表达。细心的观众可能会发现其中两个花束顶上立着两只小鸟,用艺术家的话来说:“是我个人的某种关照。”

《野放计划》
孙月 雕塑 摄影 / 德化瓷泥、摄影艺术家孙月这几年总在反复思考,从地上地下不同的角度,来观察、感受生命和时间:“地上和地下由时间所带来的感受和影响应该是完全不同的,地上有生老病死、春夏秋冬,地下是永久的黑暗,时间感是缓慢模糊的,并且是由死转生的这样一个过程。” 2017年,孙月得到在中国白瓷产区德化驻场创作的邀请,经过最初几天在德化城市边缘的“田野考察”之后,她选择了城市周边山间一小片人迹罕至的空地,完成了《野放计划》——一个地上地下的瓷土野外对比实验,此次展出的是对比实验的摄影记录。 艺术家用纯净的德化白瓷泥土制作了10个双锥,并将所有锥体的一半埋在山里的空地上。经过15天的静置培养期后,每隔5天取出一对锥体,并对地上、地下的锥体分别观测、拍照、测量尺寸、称重、记录,直到两个月后将10对锥体全部取出。地上的锥体逐渐风化变小,地下的则越来越沉,好像每天都在生长,外面是附着的黏土,里面有地下生物挖掘的孔洞。 《野放计划》试图通过一个看上去特别理性的、近似科学研究的方式,对比、描述和记录一个毫不理性的、混沌不清的、与时间流逝相关的变化过程,试图冷静地、不带感情色彩地呈现和探讨现实与认知的边界。这是一件艺术家与时间、自然共同完成的作品,用瓷土糅合自然与感知。

《无题之明珠》
(法)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 装置 / © Céleste Boursier-Mougenot / ADAGP, Paris. 致谢艺术家及保拉·库伯画廊装置作品《无题之明珠》由法国艺术家塞莱斯特·布谢-穆日诺根据明珠美术馆的展览空间全新设计。大大小小的白瓷碗在电流泵的带动下,在蔚蓝的水波中移动、相遇、碰撞、分离,迸发出陶瓷特有的清脆声音,呈现着循环、永恒。观众被邀请坐在水池边,观看流转的白瓷碗,聆听宛若晨钟的乐音,静坐凝视,进入一种玄妙的宁静状态。

《妈妈》
柳溪 雕塑 / 瓷 600×125×15cm艺术家柳溪的另一组作品《妈妈》陈列在“身体与身份”篇章,由38件大小不同、形态各异的白瓷搓衣板组成。这组持续多年创作的作品,终于应策展人之邀在明珠美术馆“”从泥土到语言——以陶瓷为媒介”展览开幕前完成,并第一次以完整的面貌亮相。 柳溪从家里妈妈用过的旧搓衣板受到触动,母亲无条件的爱与付出映射在充满时光痕迹的磨损搓衣板上。不断付出的母亲是伟大强韧的,但她同时在不断衰老,身体上又是脆弱的,这与陶瓷的特性吻合。因此柳溪收集了全国各地各具特色的旧搓衣板作为模型,制作出陶瓷材质的搓衣板,表达对母亲的爱。那些在时光中磨损的肌理、搓衣板本身的竹木纹理、带有时代与地域烙印的雕花刻印,都完整呈现在作品中。

《身体纪念碑——器》
徐鑫桦 雕塑 / 陶、牛奶 尺寸可变 * 与张春合作在作品《身体纪念碑——器》中,艺术家徐鑫桦与妻子张春用陶土拓印下彼此的身体外貌。带有身体赋形的黑陶碎片,既如同散落的花瓣,又如同容器。艺术家重新思考身体与空间关系,感悟于帛书本《道德经》中“大器免成”的非几何化空间论述。这些身体的“容器”盛装着象征生命的牛乳,将个体的身体视作对外界万物的承载。

《盛开——线系列2007 No. 11》
陈小丹 雕塑 装置 / 瓷、木箱、红色粉 200×50×35cm艺术家陈小丹的作品《盛开——线系列2007 No. 11》在“身体与身份”和“联觉与自然”两个维度之间。盛开在木箱里的大朵白色牡丹一字型排布组成“线”,牡丹花以景德镇高白瓷制成,采用捏雕手法经1300度高温烧制,花瓣极薄,美而脆弱。花与女性身份之间的联系,通过洒在花瓣间的矿物红粉进一步强化,艳丽的红让人本能联想到烈火、血液乃至其他。在陈小丹看来,这是一件无需过多文字或言语阐述的作品,她希望通过最直观的视觉感受与观众沟通,引发生命层面上的共鸣。

《移植》
梁婉莹 雕塑 / 瓷 30×30×40cm很多人的一生中总是要不断地经历迁徙。当我回顾过往的时候,总是会不自觉地用地理上的位置来划分人生中不同的阶段。不同的地理位置好像会把回忆染成不同的颜色:灰蓝、玫瑰红、明黄、浅绿。当每次浸染着所在地色彩的我们来到另外一个地理文化空间,多多少少会有点不自在的感觉。 差异在有时候是让人尴尬的,有时候又是让人兴奋的。不管是主人还是客人,都会在端茶递水的间隙暗中观察着彼此的举动和习惯。是融入新的环境中把自己隐身起来,还是继续在那种天然的不自在中保持上一次我们浸染到的色彩呢?这大概是每一个迁徙的人会不得不在身体的深处去体会的问题。

《醉》
梁绍基 雕塑 装置 / 球形化工玻璃烧瓶、陶土、氧化铁、碳、石膏、酒、熏烧、丝孰是爆裂的化工器皿?孰是怪诞的酒壶?孰是地球的残骸?孰是变异的细胞病毒?球形的化工玻璃与熏烧陶,烈酒对比中相遇,展现了当下人类的迷醉及地球的生态危机。 艺术家梁绍基的作品《醉》放在“日常与非常”篇章里,是在2020年疫情背景下,在一种非常态中对当下的反思和讨论。艺术形式上采用了综合材料,有他惯常用的代表生命轮回的蚕丝,有象征工业科技的三角锥和球形烧瓶,有贴近自然生活方式的陶器。蚕丝像白云般弥散在铝塑板上,缠绕在器皿上,在光照下泛起丝光涟漪,宛如生命呼吸在颤动。以《醉》为名,烧瓶里特意放了红色酒糟,酒味弥漫可以嗅闻,拓展作品的感官体验。而将嗅觉带入视觉艺术作品中,某种意义上这也是一件与展览第七篇章“联觉与自然”相关的作品。

《没顶曲项瓶——清雍正粉彩桃蝠纹橄榄瓶》
徐震® 雕塑 / 陶瓷 17×17×40cm“没顶曲项瓶”借鉴古代瓷器的烧制方法,将中国古瓷经典造型脖颈旋转九十度,完美呈现高难度造型,创造了陶瓷史上的新器型。这些物品的使用价值因而被完全抽离。

《生活博物馆》
徐鑫桦 工艺品 / 瓷、日常多余食材、摄影、视频、草图文献 尺寸可变《生活博物馆》是陶瓷与影像结合的作品,展陈上特别设置了可以将二者对照观看的联动空间。艺术家徐鑫桦从 2015 年开始,以一年为单位,将日常餐饮中的厨余食材,包括不同的蔬菜、水果、肉类、少量鲜花等,沉浸在瓷泥浆之中,利用相机记录其变质、腐烂、生长的变化过程,最后将泥板入窑高温烧制成瓷。通过窑火的高温烧制,食材随 1330 度的高温挥发与升华,瓷土上保留、置换了物像的“形与色”。 作品的色彩来自两个因素,一是窑炉中因不同窑位所形成的不同火痕,二是来自植物被烧尽之后遗留的草木灰(草木灰是中国古代陶瓷釉药的主要来源)。正如作品名所暗示的那样,《生活博物馆》将艺术家本人的生活体验投射在泥土之上,是以个人生活对时下社会景观的切片。

《2020》
柳溪 雕塑 装置 / 瓷、综合材料 尺寸可变2020是特殊的一年,在全球处于自我隔离和不确定的状态下,每个人都似乎是个容器,被各种情绪填满。作品《2020》利用传统器型的瓷瓶,进行切割、变形、重组,形成了新的形状,变成了承载当下情绪的容器,焦躁、抓狂、未知、恐慌、不安且抱有希望;同时像苔藓一样依附于当下状况生存。 渐变绿色描述着时间,绿色是富有生命力的颜色,而时间又有着不赦免任何人的腐蚀的力量。通过时间的考验,希望带来更多的感悟和智慧。深浅渐变的绿色瓷瓶之下,椭圆形展台以清浅青瓷色铺底,侧边涂抹近似河床泥土的藕荷色,暗藏了从泥土到陶瓷的转化与关联。

《世界啊》《星空》
赵赵 绘画 / 布面综合材料 250×200cm从宋代的建盏出发,艺术家用研究与绘画激活传统。对于艺术家而言,“世界啊”什么也不是,只是我们面对不可描述之物的讷言,不知何处缘起的情感。它没有唯一的答案,亦如艺术家的绘画所显现的,可能是微生物的细胞,可能是漂浮的沙粒,也可能是神秘而又不可知的星河。于是,“是什么”在艺术家的作品里只是一个提示,一个并不揭示本质,只是提供想象的介质。“世界”描述的不是具体形象,是无法被语言精准捕捉的感知。一个“可能是什么”的世界,一个直觉先于文本的世界。

《锦灰堆》
刘丹华 雕塑 /“灰烬”系列既写实又抽象,具有模糊多义的特征。在形象上作品逼真地再造了即将燃尽、几乎完全化为灰烬的纸张,这些聚集或散落的碎片仿佛仍在沉浮之中,似乎提醒我们文化和记忆的脆弱;其翻卷的薄片形态也犹如传统工艺中的花卉造型,比如牡丹,仿佛世间浮华的幻象正在褪去绚丽的色彩。以灰色为主调作品弥漫着沉寂、湮灭、无常的氛围,和对人生哲理的沉思。从小谙熟陶瓷工艺的刘丹华,勇于尝试和创新,挑战材料的极限,极薄的瓷片采用了传统的捏雕手法和手工釉上彩的技艺,达到了细腻而微妙的视觉效果。

《方》
刘建华 装置 / 瓷、钢 尺寸可变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方》,将工业质感的钢板与中国的传统材料陶瓷结合在一起,冷漠的钢板与金色的陶瓷是两种通过“火”的过程呈现的不同物质形态。钢有力量,但它在自然界中更容易腐蚀消失;陶瓷表面坚硬,特别易碎,但是保存更久。它们的对抗性、矛盾性及依赖性在纯粹的形式中得到体现。 艺术家寄希望作品与空间产生一种关系及情绪,人在进入空间后这种形式的感应会影响到观看方式并对一些事物的判断和认识产生一种新的可能,且有利于对现实产生一种思考。钢板上突然冒出的莫名金色“液体”,是物质在形成过程中的一个形态,这种形态的升或降也产生在人与人之间的情绪之中。时断时续的金色圆管线条,贯穿在整个空间中,像在空中镶嵌了一个“戒指”。这种物质化的形态除了能在视觉中愉悦感官,其它的只能是因人而异去体验。

《宋 建窑黑釉兔毫铜扣盏》
赵赵 雕塑 工艺品 / 穹究堂藏建窑,又称建州窑。现今遗址位于福建省北部建阳市水吉镇一带,已发现有芦花坪、大路后门、牛皮仑、庵尾山等窑场。根据考古信息及文献资料,建窑始烧于晚唐五代时期,当时以烧造青瓷为主;后至北宋初年,建窑工艺日益增进,采用凸底匣钵烧造黑釉盏,提高瓷器成品率; 及至两宋期间,建窑达到最为鼎盛时期,与宋代茶文化相辅相成,一时上至皇帝朝廷,下至黎民百姓,无不以建盏饮茶;南宋末年,御前不再以建盏赐茶;元朝起,建窑势衰乃至废止。 早在2010 年,赵赵就开始各个窑口茶道具瓷器标本及完整器的收藏与整理,10年中梳理了约30万片标本。2017 年,穹究堂开始对所有标本和完整器逐一拍摄,通过器形、字款、标本(釉色)对藏品进行梳理,针对建盏的不同类型建立档案,建立并还原建盏在两宋期间的定烧体系,研究建盏与两宋期间点茶的关系,复原及推广普及在历史中已经消失数百年的建盏所代表的宋朝汉文化。

《颜色》
刘建华 雕塑 / 瓷 尺寸可变揉泥是制作陶器、瓷器必要的准备工作,也是以陶瓷创作的艺术家、工艺美术家的基本修练。艺术家刘建华的作品《颜色》,将这一状态下的瓷泥从原始语境中抽取,它不再作为制作过程的片段。形成的裂痕是烧制时高温为它们留下的独有烙印,每个“泥团”都有着不同的恬静色彩,所谓“随类赋彩”,它们被当作独立的个体被赋予个性。

《纸》
苏献忠 雕塑 / 德化白瓷、砖 *鸣谢Ting-Ying Gallery造纸术是中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苏献忠把纸的柔软赋予瓷的坚硬之上,这正是一种对东方禅思的高级表达。从层层叠叠、薄如蝉翼而又堆积如山的“纸”中,既可见德化薄胎瓷塑的技法,又能感受到艺术家对当代精神的关注与解读,是他在探索陶瓷材料语言上的多种尝试。陶砖底座源自烧制白瓷“纸”的砖窑,陶与瓷、粗糙与细腻之间既是对比更是相生相依的关系。《纸》系列作品之一被英国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收藏。